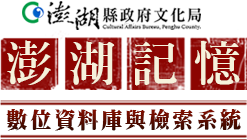澎湖縣鸞書
-
出版單位文澳歸化社從善堂
-
書名獄案金篇
-
卷期數卷一天部、卷二地部
-
開著年代1902
-
出版年1909
-
出版地馬公西文里
-
封面內容(摘要)獄案金篇黃謀烈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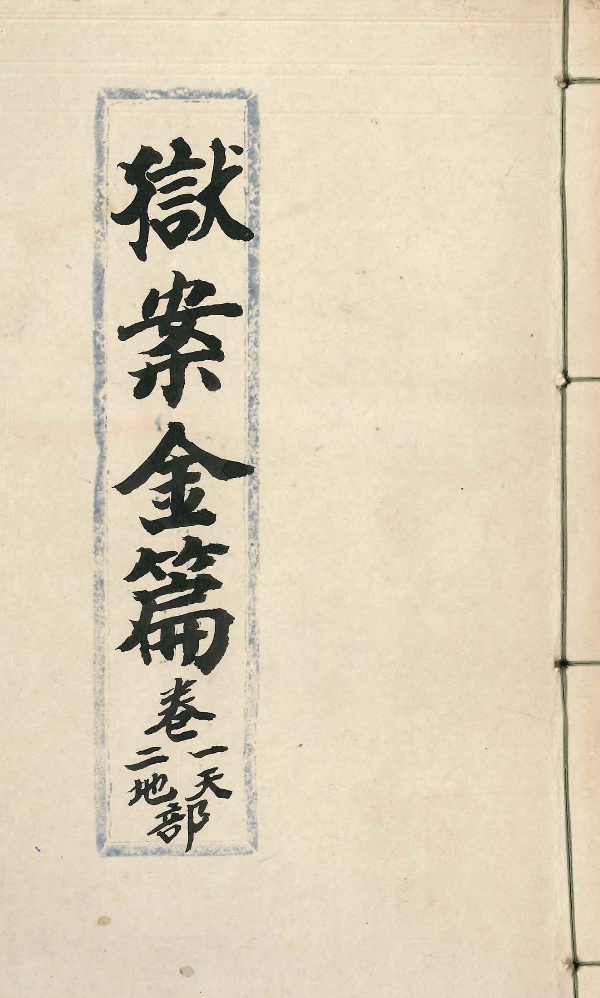
封面 / 共0頁
內容詮釋:
1895年3月23日至3月25日,日本趁馬關條約和議時機,先行出兵攻佔澎湖設置澎湖島廳,並以澎湖為對台登陸作戰船艦的集結地。澎湖自1895年3月日軍先行佔領開始,媽宮城內局勢混亂,人心忐忑不安。一新社堂主林介仁攜眷往福建同安馬巷廳山頭鄉寄居。鸞生黃濟時則退寓鷺江(廈門),鄭祖年則舉家遷返福建祖籍龍溪古郡社。而留在澎湖的一新社諸人為避中日戰禍,將扶鸞的地點由媽宮城內遷移至媽宮城外文澳之莊家,待中秋局勢穩定之後才搬回媽宮的齋堂-澄源堂繼續鸞務。
也因一新社移鸞文澳莊家,也因此結下鸞法之緣。爾後,地方人士先行組織鸞堂宣講勸善,並且選擇在莊榮(桂華)宇舍扶鸞。其次,陳積玉、莊桂華等人倡建聖真廟,聖真廟在甲辰年(1904)落成,繼之以濟世施方。以陳積玉、莊桂華為首於青蛇之歲(乙巳1905)再成立歸化社從善堂著書。然因鸞手未就,乃請石泉養善堂的許超然與陳知機協助扶鸞,書成《獄案金篇》,共分天地日月星辰六卷。故而正主席清水祖師於〈卷一〉提及:「歲維青蛇(乙巳)之歲、黑猿(壬申)之秋,疫氣頻降、飢饉薦臻,先開宣講化人,後建斯堂,隸門牆者眾有八十人。」爾後,聖廟厥成,宣講既起,因鸞學未精,陳積玉、莊桂華再行倡首設立歸化社從善堂,邀請養善堂許超然、陳知機諸人協助扶鸞。
《獄案金篇》〈卷一〉封面內頁雖然標明「壬寅(1902)仲冬著」、「天運癸卯(1903)新鐫」,然而,實際扶鸞著書的時間集中在戊申(1908)與己酉(1909)年。職是之故,《獄案金篇》的出版當在己酉(1909)年之後。
著造《獄案金篇》神明職務如下:
督造獄案總校正南天文衡聖帝翊漢天尊關
著造獄案玉勅本堂正主席加陞三級清水祖師何
著造獄案玉勅本堂副主席加陞二級文衡帝君張
監造獄案本堂慈濟真君龔
著造獄案玉勅本堂馳騁尊神康
監造獄案本境威靈城隍蘇
監壇南天靈侯太子關
掌壇本堂司禮神林
本堂迎送司紀
管理堂務供役福德神丁
把門司胡
《獄案金篇》奉派諸執事姓名臚列於左
正總董統理堂務事陳積玉
副董兼帮理堂務事莊貴華
司香兼本堂宣講生陳春桂
司香兼誦經生廖水
督辦付梓事黄修香
正鸞兼參校事許越然
録鸞正鸞兼參校事陳知機
唱鸞兼騰錄事陳勇修
唱鸞謄錄事黄慎安
副鸞兼宣講生克
副鸞生許公平
副鸞生陳養中
請誥兼備用帮唱生莊生
請誥兼進茶生莊全
請誥兼誦經生莊權
迎接知客生陳居
司茶生莊石𣞼
請誥兼傳香生莊銅
管茶生陳周
帮理宣講生陳山
接客生廖雕
誦經生莊良
迎送生陳委
司理花菓生莊立
迎送生陳獅
迎接生陳莊雲
効勞生莊標
獻帛生陳能遜
効用生莊自量
備用正鸞生陳省三
備用生黄寛柔
《獄案金篇》呈現以下特色與澎湖相關之傳說
(一) 聖真廟
文澳聖真廟落成於1902年,並以此為歸化社從善堂扶鸞之所。《獄案金篇》〈卷二〉記載壬寅年(1902)八月十五日戌刻,因從善堂鸞手未就,由許超然協助扶鸞,並訂於八月二十四日巳刻陞匾。張帝君除降筆頌揚聖真寶殿落成之美,並煩請文澳境主威靈城隍蘇撰寫聖真廟廟宇碑文。城隍蘇於同刻撰〈聖真廟落成碑記文〉。然而,落款時間卻成甲辰年(1904):
〈聖真廟落成碑記文〉
文澳之東有廟焉,額曰聖真,堂稱從善。尊奉 聖帝真君而名也!人傑由地靈,山清與水秀。溯其始兮,清水祖師開於前;步其終兮,聖帝真君繼於後。背坎面離,案山秀插,鰲頭耀南箕,東龍西虎,奎璧輝映,天星光北斗,西江浴日。萬道霞光,燦燦銀陶,東山賞月,一輪寶鏡,飄香金桂。襟澎山而帶湖海,島嶼環列星囉。連臺陽而通金厦,岡巒體勢,瀛洲彷彿蓬萊之境,依稀白雲之鄉,和哀共濟,呵氣如雲,從心所欲,平地成山。時維青蛇卜吉,始於三冬,歲轉赤馬,功成終自九夏。雖藉聖真之赫,奕實賴諸子而虔誠不吝巨款,四方成美,罔惜雕畫,一壯觀瞻。非僅頌一時之盛事,洵堪稱千秋之美舉。從茲甲第慶蟬聯,去後人文鵲起,鴻謨告竣,厥功堪紀不没諸董好善之心,遺筆千年而不朽。學愧班超,才疏袁宏,過蒙 聖真之謬舉,爰書本末以為記。
天運甲辰年仲秋月 望日 本威靈蘇拜題
(二)山水周克順的故事
山水有一座萬善廟的興建年代不詳,從《馬公市各里叢書(寺廟篇)》據聞清末時是位在今觀海別墅前的榕樹北側(舊山水漁港檢查哨)。民國49年(1960)因年久失修,由陳傳位、黃進金及值年鄉老陳水能、鮑才教、陳海豬等人發起遷建,同年農曆7月初1日落成。民國84年(1995)管理委員會又倡議重建,民國86年(1997)農曆7月2日落成。
山水的萬善廟又稱為「周克順祠堂」,從諸多有關周克順的研究,其內容大意為周克順本是駐紮在山水里的一名清朝兵勇,與百姓相處和睦,很受居民的景仰。後來聚落裡連續發生幾件少女未婚懷孕的事,卻都查不出原委,有些女孩甚至還因不堪受辱而自盡。居民發現是周克順所為,雖然曾經向周克順興師問罪,卻非其敵手。於是居民商議利用夜晚,以少女到周克順的營房前徘徊引誘,再由聚落壯丁聯合擊殺。周克順一直被追殺到海邊後死亡,屍體也赴之馮夷。周克順死後變成孤魂野鬼,搭上「王船」漂流到山水海域,打算報仇。上帝廟的主神曾經出面協調無效,後來由廟中和王爺熟識的「劉大王」出面排解,王船才轉移向龍門方向而去,事後居民為了息事寧人,就蓋了萬善廟來奉祀他。
山水舊稱豬母水或豬母落水,《澎湖聽志》云:「……東為嵵裏澳、豬母落水,最當南之衝,由陸趨媽宮三十餘里,舊有舟師戍守;今既築銃城,以防橫突……」。豬母落水為汛防重地,也築有銃城,有兵勇駐守合乎史實。然而,豬母落水有諸多女子受害於周克順而自盡,怎麼可能查不出原因或者告官追查?直到查出是周克順所為,竟以自家女兒為誘餌,合眾人之力擒殺周克順於海岸。既知周武藝高強,又有哪位父母願意以親身骨肉,身犯險境?周克順既然身犯人命重罪,鄉民將之擊殺,就情理法而言也算合理,周克順要報何讎?如此情節顯然不合理。
明治34年(1901)吳等糾合江子丹、許徽音等於西衛鄭足之厝,開設極妙社新善堂所著造的《濟民寶筏》,也記載豬母落水當地兵勇與鄉民的衝突。〈卷四〉中的「搶劫慘報近案」中的兵勇卻成為受害者而非加害者:「……此犯亦是澎廳轄下猪母水鄉人也,姓陳名勇。查生平為人,作事不合天理,行為不存良心,背倫亂紀,巧詐多端;見利忘義,糜惡弗為。……謀財害命,惡積如山;罪深似海,不知改過。至甲午年間充入營伍,越年日軍攻澎,兵勇敗北如鳥飛散,無枝可依。有一外省人姓林名全,身負一包裹,倉皇脫命,逃遁在僻壤深壑之處,凑適陳勇回家從此經過,見他素時跟官,想必有多銀可奪。正在兵燹時勢,不怕人知鬼覺,遂向前哄曰:今日若無銀與我,必要爾性命。將他拖落,周身搜銀八十餘元並一包裹亦被他拿去,致使林全淚眼汪汪,流落難歸,染病將死不願,對天哭訴冤枉。是時適有鑒察遊神稽查人間善惡,聞知此事,一一錄奏天曹。玉帝震怒,牒飛陰府冥王,今一鬼役先使其陳勇心迷意亂,狂說非為示眾,數日惡病,死於臺地……。」
此則〈搶劫慘報近案〉以澎湖甲午戰爭─乙未之役(1895)為時代背景,距離1901年新善堂著書,也才短短數年光景。〈搶劫慘報近案〉中的林全與陳勇或許是西衛鄉諸人聽聞周克順的故事後,透過扶鸞的轉譯。
文澳歸化社從善堂著造《獄案金篇》〈卷三〉記載:戊申年(1908)十二月,媽宮境主城隍廟靈應侯方降筆的「劫財害命案」,更直接指出周克順案的緣由:
「……且人生斯世,富貴貧賤由天所定,怵惕惻隱人心皆有。不義之財,一毫莫取。是語也,古人言之早矣!觀夫食婪之輩,見利而生劫奪之心,得財又思害命,天理 斲喪,良心奚存?不思人命關天,劫財者,法本難容;害命矣,罪豈能寬。嗟嗟善惡皆由相習成風,閒有仁里,轉為亙鄉。亦有亙鄉,化為仁里。所謂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理勢必然。無足怪也!吾神轄下,最無良者,莫如嵵裡澳猪母水鄉,觀其前年劫財害命一案,人心可謂窮兇而極惡。於何見之?乙未之歲,本澎慘遭兵燹,軍士風鶴流散,地方失守。由於主將老拙無能,非士卒不用命也,敗軍之士,不能憐而憫之。本自處於不仁之甚。矧敢再作逆天悖理之事,實與化外頑民無以異也。何也?時有勇營一教習士,係湖北府團姓周名克順因戍守該處地方,雖然武藝超群,怎奈虎落平洋被犬欺,該鄉鄉民人陳○○與黄○偵知他囊裡有金,先即倡首謀奪分肥,尚未思及害命。明知他旅力方剛,數人先行往試,兵刃既接,眾皆荷戈而走。雖見其英勇難敵,莫如財動人心,繼再黨率三十多輩强行迫發石如雨,必得其財而後已。奈眾寡莫敵,又兼敗兵之時,故捨其財,求保其命。誰知財奪而命難保。何則?眾思此人如此雄敵,萬一他日地方克復,吾輩必無遺類,事到其閒,一不作二不休,斬草必兼除根,逢春不能再發。今既其財,復留其命,福必旋踵而至。不如喪彼殘生而絕我等後患,計莫善於此矣!可憐周克順,乃勇營一教習士,防身尚有雙劍,先時不過欲求生命,故不下傷人毒手,他若早知該鄉懷此不良,必不能安然無事。最可恨者,鄉皆惡輩,里無善人。眾口同音,不出一言以相救。猛虎難對猴群,勢窮力竭,求生不能,被諸惡輩命送馮夷,塟身無地。噫!如此殘暴,雖鐵石心腸,莫此為甚。奚怪周克順死後英魂不散,直到地府冥王控冤,泣訴該鄉殘忍不仁,如何劫財,如何害命,如何喪身水府,如何尸居魚腹,屈冤莫伸,仰懇冥王俯憐無罪,而就死地。敢求方便准他索命,免致飛霜六月,不雨三年。冥王聽訴宽情,不覺怒髮衝冠,立即給牒,准其索命報冤,警戒後人。斯時周克順叩謝冥王,英魂即刻到鄉,公然駐鎮該鄉廟中。他乃陰曹控准,有憑有據,守境神祇不敢逆阻。飭令當境土地神將劫財害命之輩,一一查交周克順拘落地府對案,無一漏網。試觀初到索命之時,英靈赫赫,冤氣赳赳,現形變影,非法驅勢壓所能去。間有不識時務法師乩童仗法欲行驅逐,反自喪其命。所謂蟲飛入火者也。該鄉心驚胆戰未昏而門先閉,夜鮮行人,雞鳴無時,犬吠難息,恍如古戰塲鬼哭,天陰即聞。該鄉耆老又見謀害之徒,無病先後卒然而死,愈覺皇然無計可施。叩求建醮超拔等事,依然不願。無可奈何之際,齊到吾神臺前,再三求解。此冤無如惡自作者,罪當自受。無冤無讎,豈敢妄害。周克顺初速索命,曾先到案下投告,非無端而敢害人。余爕裡理陰陽,賞罰無私,有罪者宜服其辜;無過者啟容妄擾。余思今日既有此顯報,諒該郷人心亦必有歛跡,余乃代勸冤魂周克順,曰:今爾冤既伸,恨自可消,該鄉人民是 於管轄,有惡亦有善,恩怨必須分明。倘妄擾無辜,伸冤反而加罪,况對頭有主,殺人償命,理之當然。前置爾身於水府,今闔鄉既為爾超拔,諸惡謀害由爾索命,何事苛求不已。冤魂周克順聽諭,甘愿回陰。自此,鄉中日夜始見安静。報應如此昭然,人啟可妄為哉!書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是大謂歟!該鄉數年來 鄉運不振者,祇因人心作惡過多,致天地責警而如斯,勸爾世人,不義之財切莫貪,貪得財來命安在?現今謀害諸惡輩,此時俱作地獄之罪鬼,難得超轉於人世。而冤魂周克順,已判轉輪廻去了。語云:人為財死,鳥因食亡,豈不可惜哉!……。
1901年西衛鄉著造的《濟民寶筏》與1908年文澳鄉著造《獄案金篇》,均將此事的時間點指向乙未之役(1895),林全或周克順都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文澳在地理上更接近豬母落水,所聽聞周克順的故事應更為詳盡,故而能直接指出主角周克順,與豬母落水一字不差,可信度當然更高。
文中的「主將老拙無能」當指周振邦,周振邦於乙未之役慌忙乘船逃回台灣,後以「坐視不救,先行逃避」,被當朝派員押解福建,處以斬監候。而周克順為湖北府團,當時應是身懷鉅款而在兵荒馬亂之際,引來殺機。而其死於海岸,也與山水當地的傳說符合。爾後,其向冥王索牒入廟向當初的加害者報仇雪恨,造成豬母落水鄉民的驚恐,最後在媽宮城隍的勸說之下,放下怨恨轉世為人。
山水萬善廟原為有應公廟,推測本為清代義塚之類的建築。1895年乙未之役發生周克順事件之後,其屍首離落山水海岸,造成鄉民驚恐,加以當時疫疾流行,乃求諸於上帝廟主神。鄉民為其建醮超度,枯骨安葬於有應公廟。爾後,有應公廟遂有周克順祠堂之名。
(三)澎湖通判饒廷錫
饒廷錫,《澎湖廳志》做「鐃廷錫」,江西臨川人,監生。十年十月署,十二年在任暴卒。」其次,澎湖天后宮西側之陰陽堂其前身為顯靈廟。根據廟中明治40年(1907)的重建落成碑記推測,顯靈廟約於清道光年間建於文澳澎湖海防糧捕廳署旁,奉祀清代文官任職於澎湖期間逝世者,且該廳吏無後代子孫供奉香火者之牌位。饒廷錫於擔任臺灣府澎湖廳糧捕海防通判期間過世,其牌位「欽加提舉銜前澎湖粮捕分府饒諱廷錫神位」便供奉於顯靈廟。清法戰爭(1885)後,澎湖鎮總兵官吳宏洛於光緒15年(1889)將澎湖廳署遷至澎湖天后宮西側,顯靈廟亦於此時一併遷祀廳署南隅。爾後,顯靈廟發展為今日之陰陽堂。
饒廷錫究竟因何暴卒,不得而知。卻也給了當時澎湖人想像的空間,並留下負面的評價。
《獄案金篇》〈卷五〉第九殿平等王判官降筆〈圖財害命案〉,其大意為陰魂王氏控告犯官饒廷錫。此案主角王氏本為上海康有源之妻,夫開張籌緞布行生理,不幸夫妻鸞鳳分飛,子甫六歳,生理僱人代掌。王氏本欲甘心守志那知饒廷錫見王氏可愛,夫遺多金。乃圖謀王氏財產,勾引王氏,王氏乃招贅饒廷錫進門。饒廷錫繼知蠱惑王氏為其出資捐官六千金任知縣,並於福建候補。豈料饒廷錫一去之後,音信全無。爾後且對王氏惡言相向,王氏不堪受辱遂自盡而亡,並控之地府。閻羅天子准其索命。
此時饒廷錫已委任澎湖廳分府,王氏跟尋到澎。衙門乃朝廷治政之所,不敢擅入,先行稟告當境城隍飭令鬼爺謝必安、范無救引小婦到衙門,直入内堂。始即使其心神迷亂,繼則捏他魂魄,扶身持刀,使他亦自割喉而死,以還一報。
近代,薛明卿的《澎湖搜奇》亦有〈通判饒廷錫自刎之謎〉,其大意為:清朝時,有一群以饒廷錫為首的強盜。他們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所不為,令人聞之喪膽。饒廷錫等人的所做所為,官府雖有所聞,但限於地方遼闊 兵力有限,再加時局動盪不安,力有未逮。直到咸豐帝,才派遣大批官兵長期駐紮,迫使強盜消跡,居民也就得了安寧的日子。
饒廷錫本江西人,爾後流落西安城,沿街乞討。城中有一富有寡婦,對他常施濟助。饒廷錫深知寡婦是城中數一數二的富婆,每當登門乞討時,便表現出一付可憐的樣子,也極挑逗的能事。由於寡婦喪偶多年,難耐空閨寂寞,就把饒廷錫納為入幕之賓。
饒廷錫人財兩得後,即刻成為西安城頂尖人物,廣交城內各階層人物,對於仕途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憑著寡婦的龐大資源,很快地也就讓他的願望達成。他買的官職是低級的知縣,奉派到澎湖就職。這一年是清同治十年,他向寡婦表明上任後,即可將她接往澎湖同住。可是饒廷錫上任後隨即納妾,遺忘了寡婦。寡婦,後來知道他在澎湖另結新歡後,鬱鬱寡歡,最終懸樑自盡。
對於寡婦的死,饒廷錫並不知情,也不治政務,以致弄得民眾怨聲載道。饒廷錫對於與妾所生的獨生子百般縱寵,其子喜歡看戲。饒廷錫就三天兩頭的邀請戲團在縣治文澳演出。由於其兒子,時常生病,部屬為他介紹一位蔡姓中醫,替他兒子治病,但這位醫師不懂醫理,導致其子么亡,蔡醫師也就被斬首示眾。饒廷錫自從失去獨子後,精神的恍惚,經常於夜間做惡夢,卻總是夢見寡婦慘死,要找他算帳,最後竟因此而自刎於廚房。
同治5年(1866)閩浙總督左宗棠等上呈〈為恭呈辦理防勦團練暨整頓局務護解餉需尤為出力各員紳並歷屆勦辦匪未給獎敘各員弁清單事〉,其中「福建同知饒廷錫、同知銜萬棟、李鳴盛、布理問銜張光笏、布經歷銜譚承杰。以上五員均江西人,自備資斧在閩省辦理江西幫團練,在事年餘,始終出力。饒廷錫、萬棟、李鳴盛均請賞加四品銜。張光笏請賞加同知銜。譚承杰請賞加五品銜。」由此可知,饒廷錫至少於同治初年已透過捐納取得監生,並任職福建同知。任內辦理江西幫團練而加四品銜。因此,饒廷錫絕非如上述兩則故事所言,是其首次透過捐納而派任澎湖通判,在擔任澎湖通判之前,饒廷錫已任官多年。
這兩則故事,有真實的人物與若干史實為背景,當然更多的是加油添醋的成分。鸞堂在清末與日治初期代表的是知識份子階層;近代,薛明卿的《澎湖搜奇》代表的是庶民大眾的觀感,兩個不同的階層,對饒廷錫的官箴卻都是極差的評價。或許是因其不明究裡的「暴卒」,給予人不得善終,必因做惡多端的道德刻板印象所致。
也因一新社移鸞文澳莊家,也因此結下鸞法之緣。爾後,地方人士先行組織鸞堂宣講勸善,並且選擇在莊榮(桂華)宇舍扶鸞。其次,陳積玉、莊桂華等人倡建聖真廟,聖真廟在甲辰年(1904)落成,繼之以濟世施方。以陳積玉、莊桂華為首於青蛇之歲(乙巳1905)再成立歸化社從善堂著書。然因鸞手未就,乃請石泉養善堂的許超然與陳知機協助扶鸞,書成《獄案金篇》,共分天地日月星辰六卷。故而正主席清水祖師於〈卷一〉提及:「歲維青蛇(乙巳)之歲、黑猿(壬申)之秋,疫氣頻降、飢饉薦臻,先開宣講化人,後建斯堂,隸門牆者眾有八十人。」爾後,聖廟厥成,宣講既起,因鸞學未精,陳積玉、莊桂華再行倡首設立歸化社從善堂,邀請養善堂許超然、陳知機諸人協助扶鸞。
《獄案金篇》〈卷一〉封面內頁雖然標明「壬寅(1902)仲冬著」、「天運癸卯(1903)新鐫」,然而,實際扶鸞著書的時間集中在戊申(1908)與己酉(1909)年。職是之故,《獄案金篇》的出版當在己酉(1909)年之後。
著造《獄案金篇》神明職務如下:
督造獄案總校正南天文衡聖帝翊漢天尊關
著造獄案玉勅本堂正主席加陞三級清水祖師何
著造獄案玉勅本堂副主席加陞二級文衡帝君張
監造獄案本堂慈濟真君龔
著造獄案玉勅本堂馳騁尊神康
監造獄案本境威靈城隍蘇
監壇南天靈侯太子關
掌壇本堂司禮神林
本堂迎送司紀
管理堂務供役福德神丁
把門司胡
《獄案金篇》奉派諸執事姓名臚列於左
正總董統理堂務事陳積玉
副董兼帮理堂務事莊貴華
司香兼本堂宣講生陳春桂
司香兼誦經生廖水
督辦付梓事黄修香
正鸞兼參校事許越然
録鸞正鸞兼參校事陳知機
唱鸞兼騰錄事陳勇修
唱鸞謄錄事黄慎安
副鸞兼宣講生克
副鸞生許公平
副鸞生陳養中
請誥兼備用帮唱生莊生
請誥兼進茶生莊全
請誥兼誦經生莊權
迎接知客生陳居
司茶生莊石𣞼
請誥兼傳香生莊銅
管茶生陳周
帮理宣講生陳山
接客生廖雕
誦經生莊良
迎送生陳委
司理花菓生莊立
迎送生陳獅
迎接生陳莊雲
効勞生莊標
獻帛生陳能遜
効用生莊自量
備用正鸞生陳省三
備用生黄寛柔
《獄案金篇》呈現以下特色與澎湖相關之傳說
(一) 聖真廟
文澳聖真廟落成於1902年,並以此為歸化社從善堂扶鸞之所。《獄案金篇》〈卷二〉記載壬寅年(1902)八月十五日戌刻,因從善堂鸞手未就,由許超然協助扶鸞,並訂於八月二十四日巳刻陞匾。張帝君除降筆頌揚聖真寶殿落成之美,並煩請文澳境主威靈城隍蘇撰寫聖真廟廟宇碑文。城隍蘇於同刻撰〈聖真廟落成碑記文〉。然而,落款時間卻成甲辰年(1904):
〈聖真廟落成碑記文〉
文澳之東有廟焉,額曰聖真,堂稱從善。尊奉 聖帝真君而名也!人傑由地靈,山清與水秀。溯其始兮,清水祖師開於前;步其終兮,聖帝真君繼於後。背坎面離,案山秀插,鰲頭耀南箕,東龍西虎,奎璧輝映,天星光北斗,西江浴日。萬道霞光,燦燦銀陶,東山賞月,一輪寶鏡,飄香金桂。襟澎山而帶湖海,島嶼環列星囉。連臺陽而通金厦,岡巒體勢,瀛洲彷彿蓬萊之境,依稀白雲之鄉,和哀共濟,呵氣如雲,從心所欲,平地成山。時維青蛇卜吉,始於三冬,歲轉赤馬,功成終自九夏。雖藉聖真之赫,奕實賴諸子而虔誠不吝巨款,四方成美,罔惜雕畫,一壯觀瞻。非僅頌一時之盛事,洵堪稱千秋之美舉。從茲甲第慶蟬聯,去後人文鵲起,鴻謨告竣,厥功堪紀不没諸董好善之心,遺筆千年而不朽。學愧班超,才疏袁宏,過蒙 聖真之謬舉,爰書本末以為記。
天運甲辰年仲秋月 望日 本威靈蘇拜題
(二)山水周克順的故事
山水有一座萬善廟的興建年代不詳,從《馬公市各里叢書(寺廟篇)》據聞清末時是位在今觀海別墅前的榕樹北側(舊山水漁港檢查哨)。民國49年(1960)因年久失修,由陳傳位、黃進金及值年鄉老陳水能、鮑才教、陳海豬等人發起遷建,同年農曆7月初1日落成。民國84年(1995)管理委員會又倡議重建,民國86年(1997)農曆7月2日落成。
山水的萬善廟又稱為「周克順祠堂」,從諸多有關周克順的研究,其內容大意為周克順本是駐紮在山水里的一名清朝兵勇,與百姓相處和睦,很受居民的景仰。後來聚落裡連續發生幾件少女未婚懷孕的事,卻都查不出原委,有些女孩甚至還因不堪受辱而自盡。居民發現是周克順所為,雖然曾經向周克順興師問罪,卻非其敵手。於是居民商議利用夜晚,以少女到周克順的營房前徘徊引誘,再由聚落壯丁聯合擊殺。周克順一直被追殺到海邊後死亡,屍體也赴之馮夷。周克順死後變成孤魂野鬼,搭上「王船」漂流到山水海域,打算報仇。上帝廟的主神曾經出面協調無效,後來由廟中和王爺熟識的「劉大王」出面排解,王船才轉移向龍門方向而去,事後居民為了息事寧人,就蓋了萬善廟來奉祀他。
山水舊稱豬母水或豬母落水,《澎湖聽志》云:「……東為嵵裏澳、豬母落水,最當南之衝,由陸趨媽宮三十餘里,舊有舟師戍守;今既築銃城,以防橫突……」。豬母落水為汛防重地,也築有銃城,有兵勇駐守合乎史實。然而,豬母落水有諸多女子受害於周克順而自盡,怎麼可能查不出原因或者告官追查?直到查出是周克順所為,竟以自家女兒為誘餌,合眾人之力擒殺周克順於海岸。既知周武藝高強,又有哪位父母願意以親身骨肉,身犯險境?周克順既然身犯人命重罪,鄉民將之擊殺,就情理法而言也算合理,周克順要報何讎?如此情節顯然不合理。
明治34年(1901)吳等糾合江子丹、許徽音等於西衛鄭足之厝,開設極妙社新善堂所著造的《濟民寶筏》,也記載豬母落水當地兵勇與鄉民的衝突。〈卷四〉中的「搶劫慘報近案」中的兵勇卻成為受害者而非加害者:「……此犯亦是澎廳轄下猪母水鄉人也,姓陳名勇。查生平為人,作事不合天理,行為不存良心,背倫亂紀,巧詐多端;見利忘義,糜惡弗為。……謀財害命,惡積如山;罪深似海,不知改過。至甲午年間充入營伍,越年日軍攻澎,兵勇敗北如鳥飛散,無枝可依。有一外省人姓林名全,身負一包裹,倉皇脫命,逃遁在僻壤深壑之處,凑適陳勇回家從此經過,見他素時跟官,想必有多銀可奪。正在兵燹時勢,不怕人知鬼覺,遂向前哄曰:今日若無銀與我,必要爾性命。將他拖落,周身搜銀八十餘元並一包裹亦被他拿去,致使林全淚眼汪汪,流落難歸,染病將死不願,對天哭訴冤枉。是時適有鑒察遊神稽查人間善惡,聞知此事,一一錄奏天曹。玉帝震怒,牒飛陰府冥王,今一鬼役先使其陳勇心迷意亂,狂說非為示眾,數日惡病,死於臺地……。」
此則〈搶劫慘報近案〉以澎湖甲午戰爭─乙未之役(1895)為時代背景,距離1901年新善堂著書,也才短短數年光景。〈搶劫慘報近案〉中的林全與陳勇或許是西衛鄉諸人聽聞周克順的故事後,透過扶鸞的轉譯。
文澳歸化社從善堂著造《獄案金篇》〈卷三〉記載:戊申年(1908)十二月,媽宮境主城隍廟靈應侯方降筆的「劫財害命案」,更直接指出周克順案的緣由:
「……且人生斯世,富貴貧賤由天所定,怵惕惻隱人心皆有。不義之財,一毫莫取。是語也,古人言之早矣!觀夫食婪之輩,見利而生劫奪之心,得財又思害命,天理 斲喪,良心奚存?不思人命關天,劫財者,法本難容;害命矣,罪豈能寬。嗟嗟善惡皆由相習成風,閒有仁里,轉為亙鄉。亦有亙鄉,化為仁里。所謂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理勢必然。無足怪也!吾神轄下,最無良者,莫如嵵裡澳猪母水鄉,觀其前年劫財害命一案,人心可謂窮兇而極惡。於何見之?乙未之歲,本澎慘遭兵燹,軍士風鶴流散,地方失守。由於主將老拙無能,非士卒不用命也,敗軍之士,不能憐而憫之。本自處於不仁之甚。矧敢再作逆天悖理之事,實與化外頑民無以異也。何也?時有勇營一教習士,係湖北府團姓周名克順因戍守該處地方,雖然武藝超群,怎奈虎落平洋被犬欺,該鄉鄉民人陳○○與黄○偵知他囊裡有金,先即倡首謀奪分肥,尚未思及害命。明知他旅力方剛,數人先行往試,兵刃既接,眾皆荷戈而走。雖見其英勇難敵,莫如財動人心,繼再黨率三十多輩强行迫發石如雨,必得其財而後已。奈眾寡莫敵,又兼敗兵之時,故捨其財,求保其命。誰知財奪而命難保。何則?眾思此人如此雄敵,萬一他日地方克復,吾輩必無遺類,事到其閒,一不作二不休,斬草必兼除根,逢春不能再發。今既其財,復留其命,福必旋踵而至。不如喪彼殘生而絕我等後患,計莫善於此矣!可憐周克順,乃勇營一教習士,防身尚有雙劍,先時不過欲求生命,故不下傷人毒手,他若早知該鄉懷此不良,必不能安然無事。最可恨者,鄉皆惡輩,里無善人。眾口同音,不出一言以相救。猛虎難對猴群,勢窮力竭,求生不能,被諸惡輩命送馮夷,塟身無地。噫!如此殘暴,雖鐵石心腸,莫此為甚。奚怪周克順死後英魂不散,直到地府冥王控冤,泣訴該鄉殘忍不仁,如何劫財,如何害命,如何喪身水府,如何尸居魚腹,屈冤莫伸,仰懇冥王俯憐無罪,而就死地。敢求方便准他索命,免致飛霜六月,不雨三年。冥王聽訴宽情,不覺怒髮衝冠,立即給牒,准其索命報冤,警戒後人。斯時周克順叩謝冥王,英魂即刻到鄉,公然駐鎮該鄉廟中。他乃陰曹控准,有憑有據,守境神祇不敢逆阻。飭令當境土地神將劫財害命之輩,一一查交周克順拘落地府對案,無一漏網。試觀初到索命之時,英靈赫赫,冤氣赳赳,現形變影,非法驅勢壓所能去。間有不識時務法師乩童仗法欲行驅逐,反自喪其命。所謂蟲飛入火者也。該鄉心驚胆戰未昏而門先閉,夜鮮行人,雞鳴無時,犬吠難息,恍如古戰塲鬼哭,天陰即聞。該鄉耆老又見謀害之徒,無病先後卒然而死,愈覺皇然無計可施。叩求建醮超拔等事,依然不願。無可奈何之際,齊到吾神臺前,再三求解。此冤無如惡自作者,罪當自受。無冤無讎,豈敢妄害。周克顺初速索命,曾先到案下投告,非無端而敢害人。余爕裡理陰陽,賞罰無私,有罪者宜服其辜;無過者啟容妄擾。余思今日既有此顯報,諒該郷人心亦必有歛跡,余乃代勸冤魂周克順,曰:今爾冤既伸,恨自可消,該鄉人民是 於管轄,有惡亦有善,恩怨必須分明。倘妄擾無辜,伸冤反而加罪,况對頭有主,殺人償命,理之當然。前置爾身於水府,今闔鄉既為爾超拔,諸惡謀害由爾索命,何事苛求不已。冤魂周克順聽諭,甘愿回陰。自此,鄉中日夜始見安静。報應如此昭然,人啟可妄為哉!書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是大謂歟!該鄉數年來 鄉運不振者,祇因人心作惡過多,致天地責警而如斯,勸爾世人,不義之財切莫貪,貪得財來命安在?現今謀害諸惡輩,此時俱作地獄之罪鬼,難得超轉於人世。而冤魂周克順,已判轉輪廻去了。語云:人為財死,鳥因食亡,豈不可惜哉!……。
1901年西衛鄉著造的《濟民寶筏》與1908年文澳鄉著造《獄案金篇》,均將此事的時間點指向乙未之役(1895),林全或周克順都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文澳在地理上更接近豬母落水,所聽聞周克順的故事應更為詳盡,故而能直接指出主角周克順,與豬母落水一字不差,可信度當然更高。
文中的「主將老拙無能」當指周振邦,周振邦於乙未之役慌忙乘船逃回台灣,後以「坐視不救,先行逃避」,被當朝派員押解福建,處以斬監候。而周克順為湖北府團,當時應是身懷鉅款而在兵荒馬亂之際,引來殺機。而其死於海岸,也與山水當地的傳說符合。爾後,其向冥王索牒入廟向當初的加害者報仇雪恨,造成豬母落水鄉民的驚恐,最後在媽宮城隍的勸說之下,放下怨恨轉世為人。
山水萬善廟原為有應公廟,推測本為清代義塚之類的建築。1895年乙未之役發生周克順事件之後,其屍首離落山水海岸,造成鄉民驚恐,加以當時疫疾流行,乃求諸於上帝廟主神。鄉民為其建醮超度,枯骨安葬於有應公廟。爾後,有應公廟遂有周克順祠堂之名。
(三)澎湖通判饒廷錫
饒廷錫,《澎湖廳志》做「鐃廷錫」,江西臨川人,監生。十年十月署,十二年在任暴卒。」其次,澎湖天后宮西側之陰陽堂其前身為顯靈廟。根據廟中明治40年(1907)的重建落成碑記推測,顯靈廟約於清道光年間建於文澳澎湖海防糧捕廳署旁,奉祀清代文官任職於澎湖期間逝世者,且該廳吏無後代子孫供奉香火者之牌位。饒廷錫於擔任臺灣府澎湖廳糧捕海防通判期間過世,其牌位「欽加提舉銜前澎湖粮捕分府饒諱廷錫神位」便供奉於顯靈廟。清法戰爭(1885)後,澎湖鎮總兵官吳宏洛於光緒15年(1889)將澎湖廳署遷至澎湖天后宮西側,顯靈廟亦於此時一併遷祀廳署南隅。爾後,顯靈廟發展為今日之陰陽堂。
饒廷錫究竟因何暴卒,不得而知。卻也給了當時澎湖人想像的空間,並留下負面的評價。
《獄案金篇》〈卷五〉第九殿平等王判官降筆〈圖財害命案〉,其大意為陰魂王氏控告犯官饒廷錫。此案主角王氏本為上海康有源之妻,夫開張籌緞布行生理,不幸夫妻鸞鳳分飛,子甫六歳,生理僱人代掌。王氏本欲甘心守志那知饒廷錫見王氏可愛,夫遺多金。乃圖謀王氏財產,勾引王氏,王氏乃招贅饒廷錫進門。饒廷錫繼知蠱惑王氏為其出資捐官六千金任知縣,並於福建候補。豈料饒廷錫一去之後,音信全無。爾後且對王氏惡言相向,王氏不堪受辱遂自盡而亡,並控之地府。閻羅天子准其索命。
此時饒廷錫已委任澎湖廳分府,王氏跟尋到澎。衙門乃朝廷治政之所,不敢擅入,先行稟告當境城隍飭令鬼爺謝必安、范無救引小婦到衙門,直入内堂。始即使其心神迷亂,繼則捏他魂魄,扶身持刀,使他亦自割喉而死,以還一報。
近代,薛明卿的《澎湖搜奇》亦有〈通判饒廷錫自刎之謎〉,其大意為:清朝時,有一群以饒廷錫為首的強盜。他們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所不為,令人聞之喪膽。饒廷錫等人的所做所為,官府雖有所聞,但限於地方遼闊 兵力有限,再加時局動盪不安,力有未逮。直到咸豐帝,才派遣大批官兵長期駐紮,迫使強盜消跡,居民也就得了安寧的日子。
饒廷錫本江西人,爾後流落西安城,沿街乞討。城中有一富有寡婦,對他常施濟助。饒廷錫深知寡婦是城中數一數二的富婆,每當登門乞討時,便表現出一付可憐的樣子,也極挑逗的能事。由於寡婦喪偶多年,難耐空閨寂寞,就把饒廷錫納為入幕之賓。
饒廷錫人財兩得後,即刻成為西安城頂尖人物,廣交城內各階層人物,對於仕途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憑著寡婦的龐大資源,很快地也就讓他的願望達成。他買的官職是低級的知縣,奉派到澎湖就職。這一年是清同治十年,他向寡婦表明上任後,即可將她接往澎湖同住。可是饒廷錫上任後隨即納妾,遺忘了寡婦。寡婦,後來知道他在澎湖另結新歡後,鬱鬱寡歡,最終懸樑自盡。
對於寡婦的死,饒廷錫並不知情,也不治政務,以致弄得民眾怨聲載道。饒廷錫對於與妾所生的獨生子百般縱寵,其子喜歡看戲。饒廷錫就三天兩頭的邀請戲團在縣治文澳演出。由於其兒子,時常生病,部屬為他介紹一位蔡姓中醫,替他兒子治病,但這位醫師不懂醫理,導致其子么亡,蔡醫師也就被斬首示眾。饒廷錫自從失去獨子後,精神的恍惚,經常於夜間做惡夢,卻總是夢見寡婦慘死,要找他算帳,最後竟因此而自刎於廚房。
同治5年(1866)閩浙總督左宗棠等上呈〈為恭呈辦理防勦團練暨整頓局務護解餉需尤為出力各員紳並歷屆勦辦匪未給獎敘各員弁清單事〉,其中「福建同知饒廷錫、同知銜萬棟、李鳴盛、布理問銜張光笏、布經歷銜譚承杰。以上五員均江西人,自備資斧在閩省辦理江西幫團練,在事年餘,始終出力。饒廷錫、萬棟、李鳴盛均請賞加四品銜。張光笏請賞加同知銜。譚承杰請賞加五品銜。」由此可知,饒廷錫至少於同治初年已透過捐納取得監生,並任職福建同知。任內辦理江西幫團練而加四品銜。因此,饒廷錫絕非如上述兩則故事所言,是其首次透過捐納而派任澎湖通判,在擔任澎湖通判之前,饒廷錫已任官多年。
這兩則故事,有真實的人物與若干史實為背景,當然更多的是加油添醋的成分。鸞堂在清末與日治初期代表的是知識份子階層;近代,薛明卿的《澎湖搜奇》代表的是庶民大眾的觀感,兩個不同的階層,對饒廷錫的官箴卻都是極差的評價。或許是因其不明究裡的「暴卒」,給予人不得善終,必因做惡多端的道德刻板印象所致。